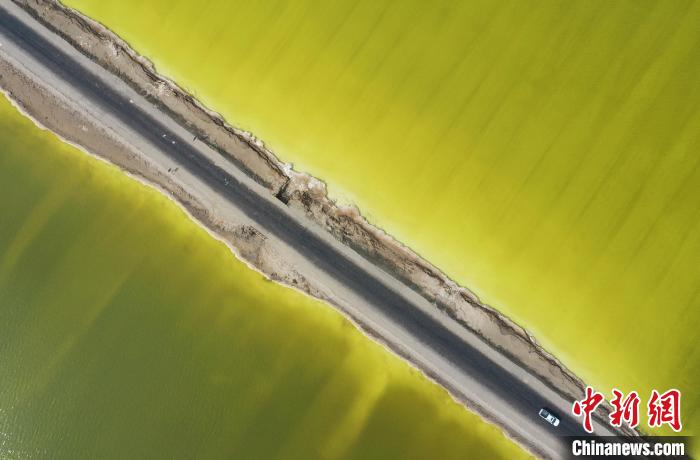乡村八音会
作者:卓然(山西省晋城市作协名誉主席)
明月,梨花,八音会,我们村子的“三宝楼台”,都在我们的藿谷洞。
藿谷洞有个梨树院,梨花开时,满院都是梨花香。八音会的老“掌皮”槐秀伯就住在梨树院,他常常把人集中到梨树院耍八音会。八音会的乐器尽管由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八种材料制成,但制作的乐器有时却不止八种,所以演奏八音会也就不止八个人。演奏八音会的时候,村子里会有很多人来看热闹,挤得院里院外都是人。人挤得太厉害的时候,八音会就移到街道上,小广场上,或者村中的舞台上。但八音会不管移到哪里,哪里都是“金色与星光共生辉,八音与人声齐沸腾”。村上人总是看不厌也听不够八音会,三天不看一回《火雷炮》,就像掉了魂一样;三天不听一回《水龙吟》,走路都没有力气了。乡村八音会的音色中包含着不羁的野性和庄严的神性,是乡村人的激情在夜色中澎湃的金色浪花;乡村八音会是一代又一代乡村人精神寄托的高山大泽,是乡村人永远仰望中迷幻的星空;乡村八音会是乡村人喜庆时的高歌,是乡村人忧伤时的倾诉与呜咽。乡村八音会别有一种情愫和风神,是乡村文化渊薮中最灿烂的一束光,是乡村文化通向世界文化园林的别一条蹊径。
凡此种种,是我对乡村八音会的体认,但我总觉得我是浅薄的,对乡村八音会的认知也是粗浅的,好在与九哥的偶然相遇,他给我讲了他对乡村八音会概括的“四音”,让我对乡村八音会有了更深刻感悟。
天地之音
那天,我刚在市中心广场旁的亭子里坐下,跟着就来了个人,大约年届古稀,虽然鬓发披霜,但骨骼健朗,穿了一身带艺术家风格的短袖衫,有点风度翩翩,却又显得手脚笨重,我想,他应该是一个久居城里的庄稼人,或者是一个带着乡村特点的城里人。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,放下时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响声,我一听就知道他背的是“八音会”的“家伙”。他把“家伙”从布袋里掏出来,一件一件摆在长凳上,拿毛巾擦擦汗。看行为,我猜他是个卖乐器的。他笑着问我:“会耍会吗?”我说我喜欢看“耍会”。他说,你是南乡人吧?晋城其他地方说“会”都是“huo”,只有晋城的南乡人说“会”是“hui”。
听他口音也是“hui”,我们便认了老乡。老乡说他姓酒,人们叫他“酒哥”,他更喜欢《九歌》,就把“九歌”做了艺名,我称他“九哥”。
九哥告诉我,他的确是农村人,高中肄业,起初是农民,后来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员,转正后,调到城里在某中学教语文,先是初中,后来教高中,再后来就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教师,再后来就退休了。九哥说,他在刚进城后,几乎每天晚上都骑自行车跑回村里去“耍会”,他们村子离城三十华里,他骑车四十分钟就回去了,耍半夜八音会,再骑车赶到学校,给学生判作业,备课,不知不觉天就亮了。几乎整夜不睡也不觉得累,好像八音会是兴奋剂一样。退休后,年纪大了,跑不动了,就买了一路“家伙”,天天到市中心广场“耍会”。我问九哥,八音会真的就那么厉害吗?你是不是太沉迷了?八音会迷了九哥的心窍了。九哥说,人都有自己的爱好,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”?
九哥不仅是个文化人,也是个深谙八音会文化的通人,我承认九哥说得对,但还是指着八音会的“家伙”问九哥,这么一大堆“家伙”,你一个人怎么耍呀?
九哥说,喜欢“耍会”的人一会儿就来了。
我说,从县市剧团退下来的老把式,都会来和九哥耍会吧?
九哥说,他们不来,他们都有职业病,听见家伙响就头疼。同时,我和他们也“耍”不到一起。我问为什么耍不到一起,九哥说,因为我耍的是乡村八音会。
我又是一惊。不都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吗?不都是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八种材料制作成的“笙、祝、鼓、箫、琴、埙、钟、磬”吗?不都是始于元末、兴于明清的“八音会”吗?怎么就有了“乡村八音会”的分别呢?
九哥没有解释“乡村八音会”,他说,他要批评我,因为我对八音会起始年代的说法是错误的。他说,八音会没有那么年轻,《三字经》上有“匏土革,木石金,与丝竹,乃八音”,作者是宋朝王应麟,说明宋朝就有了八音会;敦煌千佛洞藏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(933)写本《唐人大曲谱》,唐玄宗又是梨园之祖,在晋城望城头村如今还有“老郎庙”,说明唐朝就有八音会了;汉代许慎所著《说文》有“五声八音相比而成乐”,《诗经》开篇就是“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”,《礼记》有“金石丝竹,乐之器也”,陶钟和土埙是新石器晚期的遗物,据此,说明什么时候有了八音会呢?还有文字记载,伏羲、神农作琴,黄帝、唐尧造琴,舜作五弦之琴以歌《南风》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……”
说到这里,九哥走到亭子一侧,倒背着双手,把芭蕉扇在背后轻轻地摇着,面对热风中的竹树摇曳,仰望着未被现代建筑遮蔽的蓝天说:此论仅止于考古和文字记载,不知道隐没在荒梗烟云中的古迹还有多少,我们已经无法溯源。别说只是陶钟一片、土埙半块,任何伟大与辉煌,起初都只是个不起眼的胚胎,就连长江、黄河的源头也只是涓流一线。就是那一片陶钟、半块土埙,带着“天地之音”,降临人间,才有了惊天动地的五声八音。当我知道,我的锣鼓、我的箫声,带着神农的云影,披着黄帝的月色,带着尧的风、舜的雨,化作天地之音,穿越我的肺膈,揉搓我的肝肠,我的灵魂、我的精神,便是浮了清气,御了阴阳,与天地同和,高飞兮安翔……
九哥不仅是耍八音会的痴人,他应该是学者,是教授。面对九哥,我不仅是佩服,而是崇敬。但九哥坚持说,他只是一位耽于八音会的农人。老师也好,农人也好,乐人也好,既然喜欢八音会,他必须知道“八音会”之音从哪来,又要到哪里去了。
山水之音
至于乡村八音会,九哥说,乡村八音会既涵润着天地之音,也蕴藏着山水之音。
因为涵有山水之音,乡村八音会与宫廷、剧团、乐团,以及城市街道的八音会,便有了些差别,虽然细微,却很深刻。“八音会”这个名字既然来自经书,所以它显得有点尊贵,专业文艺团体中的人怕轻慢了它,便规规矩矩称“八音会”。乡村人也尊重“八音会”,但总觉得“演奏八音会”这样说疏离感太大,就把“演奏八音会”说成“耍家伙”或者“耍会”。“家伙”与“会”,很像八音会的乳名,叫起来无比亲切,听起来入心入肺。就一个“耍”字,如何了得!体现了自由、奔放、生动、潇洒,把人心、人性,与乾坤,与社稷,与岁月,与生命,与灵魂,紧紧糅合在一起,既收得拢,又放得开,是天容时态融和骀荡,是“草木纵横舒”,是“思逐风云上”。
把锣鼓铙钹叫“武家伙”,把琴箫管笛叫“文家伙”。文武皆备,吹打弹拨,送给我们的便是文武之德。打鼓板叫“掌皮”,一个“掌”字,明确了其地位和作用,“皮”带着“革”的气味,在历史溪流中泛着清光。筛锣叫“捣金”,“捣”的动作,“捣”的姿势,“捣”的神态和情态,想一想,就会让人惊心动魄。“揞”钹,“锯”胡琴,“砍”小锣,“咕嘟”老海,乡村人就这么说,看似字字粗犷,实则字字精神。再说,集体练习八音会,村里人叫“格研”。为什么叫“格研”,是什么讲究?查查字典,都是有学问的。“格”是纠正错误,是“格物致知”;“研”是探讨、玩味,探究事理。“格研”,似乎咬文嚼字,但村里人就这么说。
练家伙最苦的是“掌皮”,要练到手腕不动,能在小鼓中心准确地敲出清脆的鼓声。练“掌皮”把火炷插在地上,拿一双“铁筷子”敲火炷。明月照寒,鸡声破晓,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。数九寒天把手插在雪里,手都快冻僵了,方才捏着“铁筷子”练打鼓,什么时候把手练暖和了,练软了,才算一个段落。铁筷子敲火炷的声音单调而坚硬,练功夫的人心志专注而有韧劲。直练到闭上眼睛也能将铁筷子准确地敲在火炷疙瘩上,直练到手指头起水泡、血泡,生膙子,练到两根铁筷子与火炷疙瘩之间仿佛绞缠了雾一样的蛛丝,声音冰冷而清脆,且缠绵,且柔韧。等放下铁筷子,换成石竹筷子,便可以在小鼓面上随心所欲,说“走”,千军万马刀枪齐鸣;说“停”,万马齐喑鬼神销迹。练习成一个好“掌皮”凭的是意志,也会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呓怔。我们村子里老掌皮就有过练功练到老伴脊背上的故事。梦里,他在老伴脊背上敲鼓,一边敲还一边念曲牌,把老伴惊醒了,老夫妻整整笑了半夜。
在城市中,在艺术团体里,他们练家伙差不多都是对着大墙练,对着高楼练,抑或在公园里对着假山练,对着连春风都不能吹起涟沦的湖水练,所以他们的锣鼓声、丝竹声中便很少有生命活力,也少有灵魂的诗性。我们乡村里的人是对着山练,对着水练,我们的锣声、鼓声、琴声、箫声中,都是山的回音,都是水的回音。如果会欣赏,你就用心去听听乡村八音会,你便会听到山水的回声中,有山的凝重,有水的轻盈。在山与水的吟唱中,你会听到种子萌芽、枝头花开、薄暮叶落、凌晨霜生,听到黄鹂、荆翅、白鹇、锦鸡、铁棒锤儿、布谷鸟儿的嘤鸣之声……
我们在八音会的演奏中,无不带着山水之音。什么是山水之音?也可叫山水精神,也是地域特色。为什么江南丝竹多柔婉、娴静、缠绵?其音其韵,都来自杏花春雨;为什么北国的锣鼓宛若疾风骤雨,因为我们的地方多是峰峦水壑。江南丝竹是江南的山水情志,我们的锣鼓声声是我们北方人的山水精神。
为了孙子也学个好“掌皮”,他让孙子对着山练,对着水练,练出来的功夫中,那练出来的声音中,多是山水之音,天籁地籁,都是自然之声,都是山水精神。
那些牌调也多激越、高亢、洪亮。但太行山也不光是山,不光是粗犷豪放,也有山环水绕,也有细腻委婉。所以大调无比庄严无限辉煌,小令质朴风致娇媚柔曼。
没有山水之音,便没有地方风味。海内处处有八音,都是锣鼓铙钹,都是琴笛笙箫,不但式样各别,音韵也各不相同,都有自己风格,都有自己的山水之音,那是一种乡俗。
好乡有好风,恶乡有恶俗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处一个乡俗。风俗不是谁创造的,是民间发生的。我说的山水之音也许没有根据,没有来历,但我们的文化是在创造中发展的。没有创造,便没有发展。谁限止了创造,谁就限止了发展。
九哥说得那么自信,是他的文化自信,是他的民族自信,更是他的人格自信。
稼穑之音
九哥说,凡是乡村八音会,都应该有自己的“稼穑之音”。
稼穑之音不仅是坐在谷子地里,柿树下边,井台旁,念熟乐谱中的“合、上、尺、工、乙”。我所谓的稼穑之音,其实就是人间烟火,像范文正公《齑赋》中说的:“陶家瓮内,腌成碧、绿、青、黄;措大口中,嚼出宫、商、角、徵。”措大口中嚼出来的,就应该是“稼穑之音”。
九哥说,在我们村子里耍八音会的人差不多住在藿谷洞。“藿”字好看也好听,但却并非藿香之藿,乃是藜藿之藿,就是豆叶菜。过去岁月,谷是粮食,脊田薄收,交了公粮,所剩无多,全凭了藜藿来添补日月,没有一天不吃“藿羹”。“藿羹”听着很高档,实际上就是一碗“豆叶菜汤”,豆叶菜焖豆皮聊以充干饭,吃“饱”喝“足”,便去耍八音会。如果没有八音会,满肚子豆叶菜焖豆皮灌藿羹,如何消化?于是,他们就把满肚子的豆叶豆皮豆羹统统化成“稼穑之音”。一代一代的先人,怕后人把八音会忘了,就把那曲牌写在藿洞的大墙上:
万花灯 节节高 慢流 大泣颜回 柳春景 葡萄架 收江南 大开门 小开门 红绣针 石榴花……
都是这样,都是些古古怪怪的文字,并不整齐,不是一个人写的,也不是一个时代写的,有墨写的,有木炭写的,也有用红土或者老石灰写的,什么字体都有,一个字好像一个故事,说是字,又像画,泼了水墨一样,有酽的,有淡的,把一堵老墙弄得越发古老,越发苍凉。那就是我们村上的“老郎庙”,那些文字就是我们的梨之祖。每逢初一十五,都会有人把一炷香插在墙缝里,墙缝里留下一片残香与烟痕,那就是香火,那就是人间烟火,那就是他们的稼穑之音。
农闲的时候,或者下雨了,过节了,高兴了,苦闷了,闲暇了,祈雨了,敬神了,五谷丰登了,结婚、贺房、做寿、送葬,都耍八音会,都需要把“藿羹”化成的稼穑之音。
吃过“藿羹”,夜幕降临,就该去看八音会了。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灯,没有手电筒,黑天摸地的,因为要过河,因为怕狼,人们都会点个“明儿”。点个纸灯笼,点根黄栌棒儿,点一把高粱毛儿,最有趣的是点个“火笼儿”。铁丝编的“火笼儿”,与蝈蝈笼儿差不多,塞几块烧着的木炭,平常看不见火焰,需要的时候,把火笼儿“呜儿呜儿”轮几下,火笼儿立刻就成了一团火。耍八音会多在梨树院,一个大铁碗做油灯吊在屋檐下拖着两根灯捻,灯油是村人凑的,八音会的家伙也是你一升黑豆他半升黄豆凑起来买的。灯影晃动,人影晃动,一片喧哗,一片祥和。老掌皮坐在灯下,半明半暗中显得精瘦却精神,庄严得像个古铜做的古人……就这样,黑暗的乡村就有了一个个欢乐之夜,一夜一夜的稼穑之音。
村子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八音会迎回来的。数九天,天空中落着雪花,待嫁的女儿正在绞脸,上头,八音会的家伙都绾上了红绸。唢呐声中,硬是把人家的女儿吹回来,吹进了洞房。闹洞房要闹得红火,细吹细打之后,便是唱戏,唱围鼓戏。所有耍八音会的人员同时也是演员,不穿行头,也不化妆,大家围着那一面老鼓,一边吹打一边唱,唱《彩楼配》,唱《兔跳花园》,唱《龙凤呈祥》,都是稼穑之音。
有个叫海龙的老人,因为耍八音会耽搁了娶媳妇,一个光棍,一管老海,“唔嘟嘟……唔嘟嘟”地吹。人家结婚,他吹;吹到小两口入了洞房,他还吹。一个人吹。家里清火冷灶黑灯瞎火,他就对着墙吹。他爹被日本鬼子劈了,只剩几根骨头,他拣起埋到他家祖坟里,一个人坐在他爹的墓头上吹。吹得欢快时,让人想跳舞;吹到悲凉处,能把人的肚肠都揪出来。
村子里只要死了成年人,八音会都要送出村,但唯一没有送的是小青。
小青的男人是老皮,老皮也是八音会的人,但他什么乐器也不会,他是一个背鼓人,不管结婚还是出殡,老皮都去背鼓,把腰哈下,沉稳的步子都迈在鼓点里,但老皮却是八音会里最低下的人。老皮扯淡,便没有人瞧得起老皮的媳妇小青。
日本鬼子进了村,全村都跑出去躲兵,老皮把害伤寒的小青放在圈过羊的小西屋,地上铺了干草,让小青躺在干草上,他用砖头把小西屋的门垒了个结实。
日本人走了,老皮的女人就死在那个小西屋里,蜷缩得像一条干蚯蚓。老皮呆呆地看着他的女人。她太疼了。她肯定太疼了。他的心都疼了。老皮跪在地上号啕,老泪和鼻涕在那张菜色脸上纵横。
小青死后没有八音会送她,全村人谁都没有力气,也没有心情拿起八音会的家伙。但在小青死后,村上人破例四十九天都没有耍过八音会,全村人以此哀怜小青……
到第四十九天傍晚,村上突然有金声响起,与其说是有了情绪,有了心情,或者有了精神,倒不如说忧伤仍然压迫在每个人的心头,不耍一次八音会,不能缓解笼罩着整个村子里的忧伤情绪。还有,也算是哀悼小青吧。小青走时,没有八音会送她,趁小青魂灵走得不太远,给她吹打一回,让她那一缕苦魂在荒野中免受太多的孤独……
于是,在小青死后的第四十九天,村子里响起了稼穑之音。
龙凤之音
大概因为老皮和小青的故事过于悲怆,影响了九哥的情绪,九哥不再对我说话,拿起鼓槌打起鼓来。九哥不是擂鼓,是把鼓槌在老鼓面上轻敲,老鼓便发出沉闷的“隆隆”之声,忽如山风呜咽……
听见老鼓响,耍会的人陆续来了,九哥也振作了精神,又递扇子又让烟。来人有带了烟和茶具的,小折叠桌拉开,把茶斟上,不管熟人生人,各人执杯礼敬一番。人人都是那么闲适,都是那么文质彬彬。九哥对我说,他们都是农村人,都是改革开放之后进了城,说是市民,也还是农民,青枝绿叶在城里,根却牢牢在村里。他们没有忘记在村子里耍过的八音会,他们身上一直带着乡村里的“根”,走出千里万里,相隔千年万年,谁也断不了他们心里那股根。那是他们老祖宗的一脉,是他们心灵的印痕,他们即使想忘也忘不了,谁人想断也断不了。
喝过茶,八音会就要开始了,九哥对我说,他前边给我讲了“天地”“山水”“稼穑”三音,现在将听到的是“龙凤之音”,也叫辉煌之音。
九哥刚刚说罢,便听得“咣——”的一声,铜锣响了,有一点惊心动魄。
筛锣的人把铜锣高高举起,眼很专注地盯着锣心,第一声余音未销,又猛然“咣咣——”两声,锣声穿过翠竹,绕过银杏、幼松、青桐,声音仿佛是金色的。金声荡漾,从强到弱,而后归入寂静,静得让人心跳,连竹树都显得庄静肃穆。
此时此刻,看会的人也围了许多。九哥开始擂鼓了。三通鼓响之后,锣鼓齐动,如风雨交加,如电闪雷鸣,如大雨瓢泼,如山洪暴发,如一千个雷从天空中滚过,如一千条洪流奔向沟壑,像千军万马排山倒海,摧枯拉朽。金色如黄河,滔滔之水天上来,带着上苍的旨意,直指东海;峻拔如太行,孤峰高岸,壁立千仞,壮丽辉煌。一忽儿如江南的雨,一忽儿如塞北的雪。偶或薄暮将临,山鸟倦归;又如晨色乍露,鹄鸢矫翼。仿佛无比壮阔的古代战场,铁骑纵横,刀来枪往,剑戟相击。唢呐声嘶,如北马啸啸;箫声呜咽,如雁哀长空。那是一曲慷慨壮歌,犷悍,高亢,激越,似野鹤步罡,如猛虎追猎,说是精神,又是性格,也是风骨。用苏轼《有美堂暴雨》一诗形容,很是贴切:
游人脚底一声雷,
满座顽云拨不开。
天外黑风吹海立,
浙东飞雨过江来。
十分潋滟金樽凸,
千杖敲铿羯鼓催。
唤起谪仙泉洒面,
倒倾鲛室泻琼瑰。
八音会演奏到最激烈的时候,大锣、小锣、大小铙钹、一双鼓槌、一对梆子,一起抛向空中,翻腾着,旋转着,金光闪荡,像千万条金色的龙穿越飞舞在云朵中,让人炫惑,让人一时弄不清南北。等家伙落下来接在手里的时候,还来了最后一响,乐声便戛然而歇,像豹子甩尾,直如悬崖勒马。
此时此刻,街上的行人都忘记自己要去哪儿,该去办什么事了。很多人都驻足街头,或者干脆拥到小广场上来,不停地拍手叫好。
耍会的各人紧紧抱着家伙的时候,演奏并没有停止,他们似乎正在蓄势待发,或者在“养音”。“养音”这个词也是九哥的发明,即“酝酿”“氤氲”的意思,但更形象,更贴切。
稍静片刻,九哥把老鼓箭换了小鼓箭,小鼓箭在明月一样的小鼓中心,敲出来清脆的声音,锣声不再狂放,铙钹不再嚣张,各样家伙仿佛坐了十年寒窗的学子,带着斯文,带着温情,与琴、笙、箫、唢呐,文武顾盼。横笛洞箫,胡琴悠扬;杜鹃声里,春雨潇潇;喈喈者鸟歌,啸啸者马鸣;像男孩女孩走在阳光里,行在春风中,呼唤着,嬉笑着;像溪流蜿蜒于青青草下,砂石之上,石罅之间。水浒边有蜻蜓、蜜蜂、蝴蝶、青蛙、水蛇、水蜘蛛……
又一曲《水龙吟》或者《五夜城》之后,又是一通《火雷炮》,锣鼓重振山河,笙箫再焕乾坤,把人心都震碎了,让所有人都醉了。
八音会结束了。九哥站起来,对我笑笑说,这就是乡村八音会的龙凤之音,辉煌吗?
版权声明:凡注明“来源:中国西藏网”或“中国西藏网文”的所有作品,版权归高原(北京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任何媒体转载、摘编、引用,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,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 中国西藏网微博
中国西藏网微博 中国西藏网微信
中国西藏网微信